从半个天使做起——读《针尖上的天使》
这是一本极为有趣的小说,每隔一段,就有妙语。《观察家》评论此书:布尔加科夫腐蚀性的幽默和索尔仁尼琴的非凡气度的完美结合。我不知道布尔加科夫。索尔仁尼琴的三卷本《古拉格群岛》翻过半本,暴力专政的残酷无情超乎想象、极具冲击力。但资料繁复堆陈,仿佛老妇絮叨。这种感觉在看《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记实》和《大江大海1949》时重现。那些苦难,拎出任何一桩一件,都是鲜血淋漓、痛彻心扉。但是,你以为极端的个例不断升级,荒谬之后有更荒谬,惨无人道之后怀疑人道……了解苏联和我们这个国家近一百年的历史,尤其那些深埋的事件,需要强大的心脏和坚定的信念,否则容易变得麻木。那些采集素材重现史实的作者,其坚韧令人敬佩。
《针尖上的天使》却很好读。那些俏皮话甚至让人觉得作者没心没肺——这也许就是俄罗斯民族性格。而那些饱含真知灼见的话语,如此具有批判性和穿透力,以至于移用到我们的今天也非常恰当。比如这些:
——我知道你们把什么叫做小事,我责备你们的就是这个!你们对这种惨祸的习以为常说明你们对它的冷漠态度,但绝不说明这个态度是正确的。你们对当着你们的面用来捆绑人的绳索的关注不比你们的狗的脖套的关注更多。抑制你们的热望,只要你们放弃在你们国家随处主宰、歪曲一切、毒害一切的谎言,你们为人类的幸福做得就足够多了。
——光天化日之下,在众多过路人的众目睽睽之下,不经审理判决毒打一个人——这好像很自然。在文明国家,整个团体保护公民不受政府代理人专横的欺压,在这里,官员的专横要防备的是被欺侮者正义的抗议。
——为什么要怪罪一个人说他有美好的热情呢?其他人连热情也没有。
——我们早就有第二个党了——唾弃人士党。唾弃主义——是大众哲学,所有人唾弃所有事情。
——无论发生了什么事,订报人应该读到的是,我们国家一切正常。
——这个国家的氛围本身敌视艺术。一切在其他国家完全自然地产生并发展的东西,在这里只有在温室里才能成功。
——在某个部长倒台之日,他的朋友们一定要成为哑巴和瞎子。一个人一旦失宠,他立刻被当做是被埋葬了的人。
——俄国是一个讲究全无用处的手续的国度。
——一个没有公正裁判的国家是不可能有律师的。构成社会中坚力量的中产阶层从何而来呢?没有这个阶层,人民会变成被良好训练的警犬看管着的乌合之众。
——彼得堡的滨河街属于欧洲最漂亮的建筑物。成千上万的人死在了这一工程中。不要紧!但是我们会拥有欧洲首都以及伟大民族的荣誉。
——一个有能力摧毁世界的国家害怕一个奋笔疾书的小人物。
——真相妨碍像以前那样盲目地相信。
——宣传是人类已知的最不道德的事业之一。
——一个怪圈:上面的人以为,下面需要谎言,而下面以为上面需要。
——如果后代称呼我们的时代,那么不会是原子时代,不会是航天时代,而是伟大的造假时代。
——这片土地凭苦难和忍耐,老兄,也许比任何其他土地更应该从上帝那里得到更正派的政府,和报刊……但是……
——(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特派员:)不刊登别人的东西原来比刊登自己的东西甚至更有意思。
——什么是一般的媒体?这是三大原始功能:报道,启发与娱乐。我们的任务要复杂一些:以假报道蒙蔽,模糊,让人困惑不解……
……
小说描写的人物主要是虚构的中央报《劳动真理报》的编辑和记者——一群“笔杆子”。其中最传奇的一位笔名塔甫洛夫。他幸运地从斯大林时期的集中营活过来,并担任了该报共产主义教育部代理编辑。小说称,他“替所有人写过并且写过所有人,可关于他(如果不算告发信)从来没有人写过”。
其经典一役是一次青年思想工作会议。会议快要开始了,但部分报告却要重写,塔甫洛夫到达现场,问清主题之后,开始向打字员口授报告。口授完了谁的稿子,那个发言人就要求发言并爬上讲台。英雄宇航员加加林突然出现,挑战了一下这个身经百战的笔杆子的功力上限——在大厅起立鼓掌欢呼加加林的时候,他口授完了加加林演讲的第一页。加加林念第一页时,他开始口授第二页。但是加加林念完第一页时他还没完成第二页。加加林看着主席团。会议大厅于是持续鼓掌,直到他口授完第二页。
塔甫洛夫有一个和唐朝诗人李贺收集佳句的“锦囊诗袋”类似的装置——意克拉。这是他的意识形态结构模型,一套从报纸上剪下来的词、句子、引文和整个段落,并按主题排列在一个纸盒里。每次替人捉刀,他从中取出主题思想撰文,之后再充实意克拉。
塔甫洛夫是犹太人,但是被身份证登记员错写成了印杰伊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民族。然而后来他被抓,其罪名是“为印杰伊共和国从事间谍活动”。此后,他又不得不承认,自己是这个共和国安全部门的情报站站长。他害怕还要在地图上指出这个国家所在。不过调查人员没有强迫他这样做,但还是纠正了他:“你不是情报站站长,而是被情报站长们策反了,明白了?”
尽管塔甫洛夫简直是苏联的胡乔木,但由于犹太人身份等污点,终身不得志。其部门代理编辑的职位,还是在主编马卡尔采夫的庇护下取得的。马卡尔采夫能身居此位,并成为中央候补委员,因为他这个笔杆子极富主观能动性,并且善于自我洗脑。从攻击法西斯到斯大林勾结希特勒的巨变令他反思:
童年和少年时别人教育他,到后来他教育别人,用的都是反法西斯主义。可现在呢?表面上似乎一切照旧,可里面已经不同了。他感到,如果领悟到斯大林同志总政策关于今天的部分,他将是胜利者。他今后的全部道路,他最大限度奉献的机会现在都取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正确地执行国家乃至全世界领袖的显然在胆略上是天才的意图。要知道斯大林并非偶然的宣布,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阶段。就是说,现在需要与法西斯分子携手工作。
他也经历了一个初出茅庐的记者到可靠的“把关人”的转变:
年轻时马卡尔采夫痛苦过,他感到,他个人的尊严有时由于必须执行荒唐的命令而受到侮辱。因此他找到了出路:尊严不受损害的前提是,如果他本人还在决议之前就能领悟,在此刻什么符合上面的精神,什么不符合。而不好的、智力有限的领导在等候指示。
我们现在有进取心的党报领导,如果参考马卡尔采夫的心得,奉之圭臬,也就能像他一样,无论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相反,都是掌权者心目中的“自己的人”。
尽管如此,马卡尔采夫缺乏安全感。小说的开头他心脏病突发,倒在中央委员会的门口。其原因是,他有一天突然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本非法出版物。他六神无主,疑心有人抹黑,或者是上面故意试探。五内俱焚加上无产阶级领导惯有的、为革命事业无限操劳导致的恶劣健康状况,令他突发心脏病。
击倒主编的这本非法出版物标题是“1839年的俄国”。书由法国外交官用法语写就,记者伊弗列夫将它翻译成俄文并偷偷散发。这本写于小说时代背景(1969年)之前130年、攻击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的书籍,在其时仍然“荣膺”“反苏非法出版物”之列。这是因为,“这是现在还是在1839年写的,难道有什么区别吗?通过仔细观察这可以看出来!”(书中马卡尔采夫语)这为后来史称苏联的“停滞时期”,提供了恰如其分的佐证。
1964年赫鲁晓夫被逼下台后,勃列日涅夫成为苏联第一书记。但是,他除了积极安插心腹,巩固权力之外,尽力维稳,反对改革。在1968年-1969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了布拉格之春之后,保守政治的势力更加稳固。在勃列日涅夫统治的18年间,苏联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停滞。
然而,小说借“1839年的俄国”一书所指的“停滞时期”,时间持续更久。这个无产阶级政权与此前被推翻沙皇统治,一样“靠谎言生存”;“讲究全无用处的手续”;“撒谎意味着保护,说真话意味着动摇基础”;“人民在默默的酗酒中浇灭自己的忧愁,上等阶层则是在喧嚣的狂欢作乐中”。
“通过仔细观察”,也不难看出《针尖上的天使》所述的情况很像中国,尤其是这群笔杆子所承担的“党的喉舌”的作用。他们热衷于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宣传;策划能向上邀功请赏的活动;树立宣传各行各业的“模范”;国内形势一片大好,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生活悲惨;封杀所有负面的新闻……他们的新闻观念或者说宣传观念,仍然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为读者是任由摆布的靶子,宣传的枪炮一经打出,必能命中目标,并起到相应的反应,甚至支配其行为。然而,百姓根本不相信报纸所说。即使《劳动真理报》的印刷工人,都唾弃自己的报纸,在家里用收音机偷听外台获取信息。
马卡尔采夫一类的笔杆子,主动学习,与时俱进,将自己很好地嵌入到了宣传机器当中。但是作为螺丝钉,他们仍不够合格。马卡尔采夫一心想去掉中央委员前面的“候补”二字,但不能如愿。《劳动真理报》的副主编亚古博夫评价他,“扮演的是知识分子,换句话说不过是落后于时代。”而报社以塔甫洛夫和伊弗列夫为代表的一批员工,同样“自诩知识分子”,而被亚古博夫列入清理的名单。
“知识分子”身份和新闻工作者在苏联是冲突的,在中国的某些历史阶段同样如此。和马卡尔采夫身份相当的《人民日报》社前总编辑邓拓,1957年就被毛泽东批为“书生办报”。因为当时的人民日报在宣传共产党的最新“精神”方面迟钝、肤浅、“战斗力不强”。邓拓文人本色,品格正直。“大鸣大放”之际,就写杂文批评贪大喜功、缺乏实际意义的“庸人政治”。他从事宣传同样鞠躬尽瘁。即便在他自己的诗篇中,也总是讴歌壮丽山河和群众力量。甚至在自杀前遗书末尾,不忘高呼:“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参见袁鹰《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
三年前,我还是一个党报新闻工作者。党报举行“读书写读后感”活动。我读了《风云侧记》之后,如是写道:这些优秀的报人和知识分子,即便才华横溢、正直善良,但当政者犯错直至荒谬的程度时,都没有“纠错”的思考和努力。
我这么写当然是苛求古人,但事实恐怕确实如此。《风云侧记》当时也传被禁。新闻出版署虽然否认,但承认禁止其再版。马卡尔采夫在自己办公桌上发现一禁书,吓出心脏病。如今我能公开看禁书并写读后感——历史确实在进步。从这一点,我能理解一些前辈所说的“80后”预期高而导致的幸福指数低的逻辑。不过,看《针尖上的天使》《风云侧记》让我想到,当人们从“莫谈国事”的禁忌中走出,重新履行风议时政的传统与责任,非常难得。国庆期间,温家宝数谈政改。许多人批评其光说不练。但崔卫平等人在微博上指出,关键还要看我们公民做了什么。我们也有参与的义务与责任。我深以为然。
塔甫洛夫和伊弗列夫亦师亦友。前者将有限的才华投入到了无限的宣传工作当中。在和伊弗列夫的谈话中,他对自己的身份做了概括:
“我不知道,记者这是什么职业……我个人的职业是说谎者。并且在我们这里没有碰到过别的如您的尊口所说的‘记者’。”“他们自己撒谎的文化水平不高。所以我算是个好文字匠。”他所求的,只是“在这样一个服苦役的地方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曾用所罗门国王宝戒上的话“一切都会过去的”来自我安慰,但伊弗列夫被捕后,他说,“要是我有宝戒的话,我会在上面刻上:‘这一切都不会过去的!’”
塔甫洛夫曾对伊弗列夫说:“就让像您这样的人奋斗吧。”但塔甫洛夫后悔自己如此地影响了伊弗列夫。伊弗列夫寄希望于死寂的现状出现裂缝。他不甘于抱怨,成为一个行动者。借到各地采访事迹、成就的机会,他收集地方人员口中所说的“这个不要记录”或者“这个不要刊登”的素材。当报社的摄影记者被警察无故暴打并拘留时,他写了一篇揭露事件真相的报道准备刊登,却被亚古博夫的犬牙——设在报社的报刊保密检查员发现并阻挠。最终,伊弗列夫翻译并传播《1839年的俄国》一事被克格勃发现,遭到逮捕。亚古博夫事先得知他将被捕,迫使伊弗列夫辞职,借口是“因个人不谦虚的言行”。而凡是被这一条理由辞退的员工,无法提起诉讼,因为法院被禁止审理涉及此条款的不公正辞退案。
本书的作者德鲁日尼科夫说,伊弗列夫等这些试图改变现状的人,正是小说标题中的“天使”。作者在正文前引经院哲学课本中的话:“针尖上能够容纳的天使数量等于2的平方根。”2的平方根,等于不到1个半。万马齐喑的苏联停滞时代,“天使”的数量就这样。本书中,伊弗列夫算1个,塔甫洛夫等其他一些人只能算不到半个。此外的芸芸众生,则是魔鬼和魔鬼的奴仆。
关于“针尖上能站多少个天使”的问题,有哲学家说,由于天使的体积、质量不可度量,也许,针尖之上,天使无数。在中国,和小说类似的时代,离去不远。我们也能看到那些令人不满的“停滞”。但是,天使为数不少,即便在我的微博所关注的那些人里,就有许多希望推动社会变革的人们。他们不仅是知者,而且是行者。我自己呢,虽然做不了什么,但是围观、唱和,就从半个天使做起吧。
《针尖上的天使》,[美]德鲁日尼科夫著,王立刚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5月第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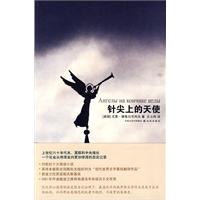
作者简介
尤里·德鲁日尼科夫(美国),俄罗斯作家、散文家及文史学家。1933年生于莫斯科一艺术家家庭,中学期间因对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评价不足而受责难,导致随后没有一所莫斯科高校愿意录取他,后入拉脱维亚大学学习,最后在莫斯科国立师范学院历史语文系毕业。他当过教师、图书编辑、报社记者。1971年加入苏联作协。1977年因从事地下出版等活动而被开除出作协,后流亡国外,在维也纳逗留一年后前往美国。2001年被波兰推荐角逐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长期担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及国际笔会美国分会副主席。他的作品中俏皮的双关语层出不穷,包含双重、甚至三重的心理动机的潜台词颇显优雅,善于在悄然无形中从严酷的现实转向卡夫卡式的变形夸张。他的作品体裁多样,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针尖上的天使》、微型长篇小说《沙皇费多尔之死》、短篇小说《为什么要烦普希金》、戏剧《老师恋爱了》等等。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